剧本《沉钟》是盖哈特·霍普特曼(Hauptmann)于1896年创作的一本象征剧,讲述了铸钟师亨利渴望山上响起他的钟声,但在山上铸钟的理想生活和山下的世俗生活之间摇摆,最终因看到妻子的眼泪,放弃铸钟梦想而死去的故事。
1925年,杨晦先生读到该剧本,深怀感慨,于是提笔写下评论文章《沉钟》,发表在《沉钟》周刊第一、二期。而“沉钟社”以及《沉钟》杂志之名,也正是借自该剧本,以剧中人铸钟者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。周刊创刊号首页眉端复引英国作家吉辛句:“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……我要工作啊,一直到我死亡之一日。”凡此,足见该社之风格与特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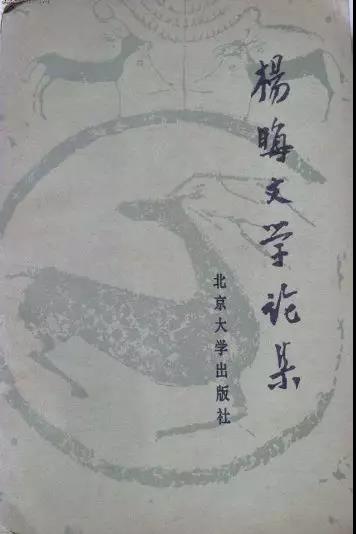
杨晦文学论集
杨晦先生在文章开头写道:“《沉钟》这剧本,在我,也好似一口沉了的钟,有许久都沉埋在我那书架的深处,不曾听到它的鸣声了,虽然在我的脑海里还荡漾着它的余波。”那个时候,他在朋友的谈话中忽然感到一阵复杂的心情,听到远方的晚钟,不由得想起《沉钟》这个剧本以及一些往事。
谈到剧本,杨晦先生多半怀有深沉清冷之感,或许是唤起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,扩而广之,“认识了人类共同的运命”。人类的命运不同而又相同,酸苦辣应有尽有,命运女神却不曾多给我们一些甜味。然而我们安然生活着,看着其他人,看着上一辈和下一代,因袭陈规传承惯例。但命运女神偏又不肯善罢甘休,在人生黑暗线上露出一些光明色彩。我们能够在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中看到光明,在深夜看到月亮和星星,“在黄昏的时候,我们也许就预想到了天明。沙漠中偶尔也遇到了绿洲,阴雨天反或看见了彩虹。”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“绝望之于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。”希望的幻影让我们忘却身处的黑暗,故事中的亨利也不会终生在山上生活。
和山上相对,山下生活意味着陷入尘世,而尘世中充满了复杂的关系,我们需要面对琐碎而繁多的事物,关键在于我们无法摆脱。杨晦先生因此感叹道:“人类只是这样的不幸而且可怜!”这或许是从古至今一个永恒的命题:现实和理想发生冲突时,我们应该如何取舍?杨晦先生假设,如果亨利能够残酷无情,在艺术或者社会中,他都将占有最后的胜利。但我们人类即使知道这一点,但我们不得不看着自己陷入无可避免之中。而特殊的一类人——艺术家,在社会中面对的问题更加突出,“他的理想,超出了现实,他的生活却离不了现实”,所以,“艺术家的生活,往往只是一个冲突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他只是孩子的爸爸和妻子的丈夫,沉钟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。在剧本之中,妻子让孩子带着自己的眼泪来寻丈夫回家,丈夫便直接感受到了个人的微弱和联系的难以割舍,人生一变而苦痛,忧伤。他终于回到山下,但他却完全忘不了理想的钟和精灵(一说是林中女妖)。然而钟是不可能再铸造的了,梦想的破灭也让他失掉了内心的和平。当他再次回到山上,看到悲凉伤感的空山,不由得哽咽凄婉,悲悼过去和将来,感受到命运的残酷。于是他在象征理想的精灵怀中,朝着成为虚无的梦想前进了。
亨利的悲剧给人一个启发:艺术家若要完成自己的理想,必须全力以赴,弃绝一切世俗生活的干扰。1925年,几个青年人听到远处的晚钟,便怀着把沉入湖底的钟撞响的精神,将刊物命名为《沉钟》。而事实上,之后他们也确实为《沉钟》周刊的生存而奋斗。陈翔鹤在《沉钟》周刊第五期发表《彳彳彳……》一文:“在三月以前,就决定了将我们沉下了的那口钟,重新的掘起来,不管喑的声音是怎样的,咽(喑)弱低暗,然而钟仍是钟,就是敲成了碎片,它依然是不失其为钟……”而鲁迅先生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·导言》中也评价道:“在事实上, ‘沉钟社’ 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, 最诚实, 挣扎得最久的团体。它好象真要如吉辛的话, 工作到死掉之一日, 如“ 沉钟”的铸造者, 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……”
而在怀抱沉钟精神的青年人中,杨晦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“钟”奋斗,在现实和艺术之间,在工作和创作之间,在美善与责任之间,他的坚守执着,始终提醒着我们,希望与命运的辽阔,和钟声的悠远。
参考资料:
杨晦:《沉钟》,《杨晦文学论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-10
张晓萃.沉钟社始末[J].新文学史料,1987(03):54-66.
作者:中文系2016级本科生 张灵凤
编辑:蔡子琪
文章图片源于网络
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编辑处理
zhongwenxi@pku.edu.cn